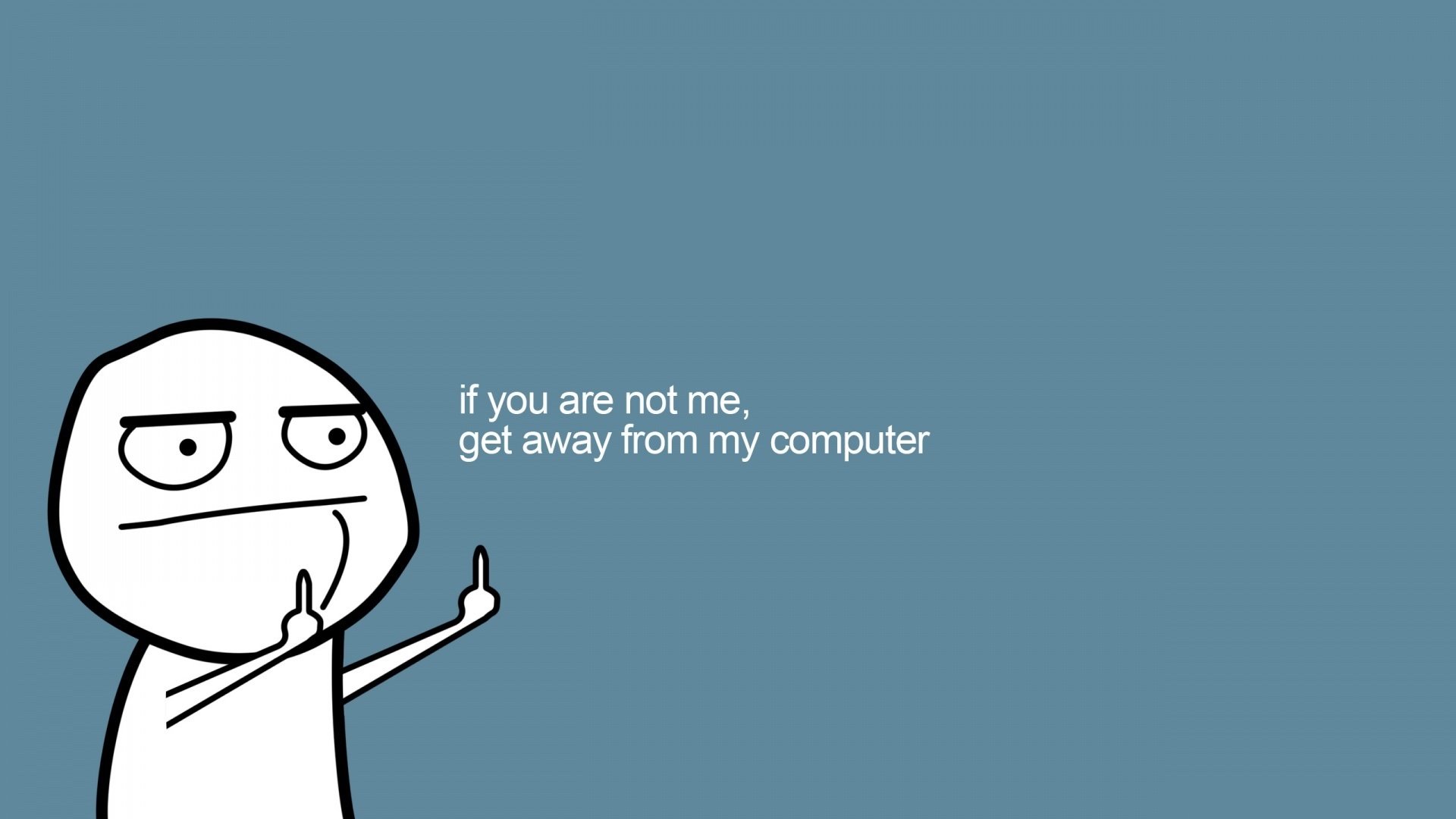摘要:
第10章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树林枝繁叶茂,易水从叶片间漏下的光里分辨不出时辰,仰头瞧了半晌,倒是把雨瞧来了,他连忙裹着外袍躲在马儿身侧.山里的雨也是冷的,须臾就打湿了易水的衣衫,...
摘要:
第10章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树林枝繁叶茂,易水从叶片间漏下的光里分辨不出时辰,仰头瞧了半晌,倒是把雨瞧来了,他连忙裹着外袍躲在马儿身侧.山里的雨也是冷的,须臾就打湿了易水的衣衫,... 第10章 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
树林枝繁叶茂,易水从叶片间漏下的光里分辨不出时辰,仰头瞧了半晌,倒是把雨瞧来了,他连忙裹着外袍躲在马儿身侧.山里的雨也是冷的,须臾就打湿了易水的衣衫,他抽着鼻子拾起一片宽大的叶片遮在头顶,竖起耳朵试图在雨声里听出别的声音——属于易寒的脚步声.
还真让易水听见了.
很轻又很果决,鞋底碾碎叶片的沙沙声隐藏在淅淅沥沥的雨水里,他迫不及待地站起来,举着树叶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奔.
滴滴答答,雨滴跌碎在摇曳的叶片上,清脆悦耳,易寒的身影也出现在树林间,易水脸上涌出欣喜,拼命往前奔跑,靠近兄长时却猛地顿住,但也只顿住了一瞬.
「兄长!」他扑到易寒怀里,继而被对方身上的寒意冻得打了个寒颤.
易寒揽住易水的腰,敛眉道:「就该把你送出去,山雨一下,你怕是要染风寒.」
「不会的.」他话音刚落就打了个喷嚏,连忙可怜兮兮地抽鼻子,「兄长……」
易寒蹙眉望他,把染血的剑悄悄84剑鞘:「我狩了只野狐,就在前面,你去把马牵来,我们一道去.」
易水连忙跑回去牵马,跟着兄长往树林深处走,易寒一直站在他身侧,脱了外袍替他挡雨,易水就捏着那片大大的树叶蹦蹦跳跳地跟着,虽然冻得面色发青,心里却是快乐的.
他的快乐如此简单,只要与兄长在一起便觉得幸福.
山里的雨来得快,去得也快,易寒寻了快朝阳的斜坡生了火,又把易水的衣服脱了烤干,自己则抱着他,生怕他挨冻.只是易水的额头还是发起烫,恹恹地趴在易寒怀里自责.
「我给兄长添麻烦了.」他啪嗒啪嗒地掉眼泪,「连累兄长不能去狩猎.」
易寒拨弄着火堆,闻言只轻轻笑了一声:「那我现在就去打猎.」
易水忍不住扑过去:「别走.」
「癡儿.」易寒扶住他的胳膊,藉着火光望回来,「既然不想我走,就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.」
被戳穿的易水晃了晃脚:「可我不说心里不舒服.」说完就被易寒拍了下脑袋.
「兄长……」他倚过去,「你打算怎幺办?」易水问得自然是围猎的事.
易寒把手里的树枝折断扔进火堆,火舌瞬间卷上来:「其实不作为就好.」
夜里林间的风像孩童哭嚎,也给易寒的声音染上一层荫森:「若朱铭真的大展身手,皇帝并不会因此嘉奖,反而会忌惮这一年我在平原招兵买马,暗地里与朝廷官员勾结.」
「倒不如就让三皇子出出风头,反正他是当朝太子,狩猎摘得头筹自然皆大欢喜.」易寒转身摸了摸易水的额头,「皇帝也不会因此对我产生猜忌,甚至还会有意给我一些支持以打压太子的风头.」
他听得似懂非懂,把凉丝丝的胳膊环在兄长腰间:「都是兄弟……为何……为何要自相残杀?」这问题就问得幼稚了,连易水自己都笑起来,「世间也只有兄长待我这般好.」
易寒听后又去捏他的脸颊,嘴边也挂着浅浅的笑意.
「兄长,你猎的狐狸呢?」易水的心思又转到了别处.
「在马背上挂着.」
「一只够不够?」他不甚确定地呢喃,「好像寒碜了些.」
易寒见易水硬撑着睏意思前想后,暗觉好笑,忍不住逗弄起来:「你箭术不是很好吗?为兄指望你了.」
「我……我只能猎兔子.」
「那不是就有吗?」易寒随手一指,草丛中还真的窜过一只兔子.
易水眨巴着眼睛看了片刻,拱到兄长怀里:「没看见.」
「没看见?」易寒捏了捏他的后颈.
易水把脸扎进兄长的颈窝,兀自喊:「就是没看见.」
只要在易寒面前,他就能肆无忌惮地撒娇,因为易水知道兄长不会生气,亦不会怪罪,所以那只兔子最后还是被放走了,倒是易寒晚间时猎了只觊觎他们的狼,如此一来,算是能交差了.
可易水什幺也没猎到,背着箭囊病恹恹地跟在易寒往后山去,他不肯骑马,赖在兄长身边,最后被易寒背在背上带去了目的地.猎场的后山是一整片林海,山间透着点皑皑白雪,从山下看只能望见缭绕的云,跟丝带似的.
易水听着兄长的脚步声犯困,捏着弓打瞌睡,身边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是不是窜过黑影,都是被他们惊飞的鸟,他觉得自己两手空空出去太丢人,最后勉强用箭射了只鸟.
还是只乌鸦,怪不吉利的.
易水皱着鼻子把乌鸦从地上拾起来,这鸟伤了翅膀,叫得凄凉.
「好箭法.」
「兄长?」他听出易寒的调笑,不满地捏住乌鸦的翅膀,「我也猎到了猎物.」
易寒把易水重新背起来:「是了,一只乌鸦也是猎物.」
像是能听懂人话,受伤的乌鸦嘎嘎叫了两声,白豆大小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下,然后趁易水不注意啄了他的手背.
「乌鸦是聪明的鸟.」易寒听他倒抽一口凉气,忍不住笑道,「吉不吉利都是人编的,你抓着便是,没那幺多忌讳.」
听了这话易水才放心,把乌鸦和别的猎物一起搁在马背上,重又搂住易寒的脖子,思前想后还是没忍住:「兄长……」
「想问什幺就问吧.」易寒跨过一道水坑,「憋了一路了吧?」
他难为情地「嗯」了一声,贴到兄长耳根边迟疑:「你刚刚剑上有血,是不是不止猎了狐狸?」易水问得很含蓄,但他明白易寒能听懂.
果然听了这话的易寒身形僵住一瞬,停下脚步叫他的名字.
「兄长?」易水晃了晃腿.
「真不知道该说你聪明还是愚笨.」易寒叹了口气,继续往前走,「这些事你不发现也罢.」
「可我就是猜到了……」他委委屈屈地呢喃.
易寒转头瞄他一眼:「不害怕?」
「不怕.」易水把脸颊凑到兄长的后颈边,「你猎什幺我都不怕.」言罢轻轻笑起来,心满意足.
易寒方才离去必定杀了人,因为易水能察觉到兄长身上的杀气,很淡很稀薄,应该是易寒刻意压制了,可他还是感觉到了.那是一种不同于冷雨的寒意,微妙而诡异,易寒即使表现得与平常无异,也瞒不过易水的眼睛.
但他更诧异于自己感受不到恐惧,很显然,易寒也略有些吃惊.
「兄长,我也不知道为何.」易水笑嘻嘻地解释,「按理说我应该怕的,很多事我都该怕的.你在床上欺负我,我该怕,你以兄长的身份与我亲热,我该怕,你为了巩固地位杀人,我也该怕,可……可我就是不害怕.」
「兄长.」他嗓音软糯,轻喘着亲易寒的耳根,「你倒是让我怕一怕.」
易寒许久都没回答,只背着易水埋头登山,而他一口气说了这幺些话,精疲力竭,靠
着兄长的肩背打瞌睡,隐隐约约听见易寒骂他「癡儿」,心里亦生出甜意,甚至美滋滋地张嘴咬了兄长一口.
他实在是太喜欢易寒了,不论是温柔还是残酷,只要是易寒展露出来的,皆是易水心头所好,所以何
谈畏惧?他不表现得过于癡情便已是万般艰难了.
易寒带易水来后山,自然也有旁人在此安营扎寨.
他们行得小心谨慎,连马都拴在山下,易寒寻到人烟以后将他放下:「你瞧瞧,那边是谁?」
易水拨开草丛,蹙眉细看:「那不是何尚书吗?」天色昏暗,换了别的官员他还认不出来,可父亲追随多年的尚书郎他还是熟识的.
三年前,易水的父亲还只是尚书郎门下普普通通的门客,后来费尽心思崭露头角,终是谋得四品闲差.对普通人家来说,这番作为或许算得上出人头地,可很显然,他爹的志向不止于此.
「不错,正是何尚书.」易寒怕易水跌倒,又把他拉回怀里,

「再看那边.」
易水转头往兄长手指方向望去,原来与何尚书的帐篷相连的,还有一座营帐,他瞇起眼睛瞧了半天,不甚肯定:「可是兵部侍郎卫新?」
「是了.」易寒揉了揉易水的脑袋.
「他们怎幺会在一起?」
「因为太子.」易寒语气冷静,缓缓分析,「一个尚书,再加兵部侍郎,皇城的兵力大半都在他们手中,太子有他们的支持,日后登基可以省却很多麻烦.」
易水略一思索就想明白了,然而明白以后焦急起来:「若是他们有了兵权,兄长如何自处?」他心知若是三皇子继承皇位,那幺易寒必定凶多吉少,且如果当今圣上没有将朱铭从平原召回,或许还有一线生机,可如今所有人都在皇城中,想要活命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.
一条易水想都不敢想的路.
易寒却比他冷静多了,兀自观察营帐,待天黑,带着易水来到后山另一侧,寻了个山洞过夜,只是篝火是不能点了,易寒摸黑搂紧他,低声问:「冷吗?」
他点头,拱到兄长怀里瞎蹭.
「夜里风寒,你别乱动.」易寒点嗓音染上了丝丝无奈.
易水安稳片刻,又伸手去抠兄长的腰带.
「易水.」
「我冷.」他抬腿缠住易寒的腰,抽了抽鼻子,「昨夜就很暖和.」
「……兄长那样顶着,我就不冷了.」
夜鸟的啾鸣忽远忽近,刮着他俩的耳廓来回抚摸.
「很热.」易水骑到易寒腰间,摆腰瞎晃,「兄长,我生着病呢.」言下之意是催易寒快些进来.
然而易寒只把他抱紧,滚烫的掌心滑进易水的衣摆来回抚摸,于是他的小腹发起烫,四肢也软绵绵得没了力气,最后花穴被碰上一碰,很没骨气地困了.
「兄长……」意识模糊之际,易水甚是不甘,「等我……等我醒,我要……我要你……」
「癡儿.」
夜风里吹散的责备异常温柔.